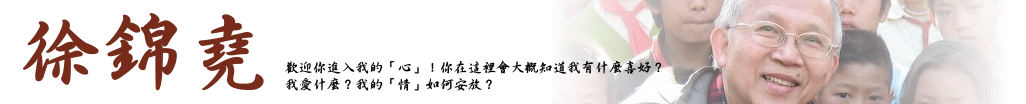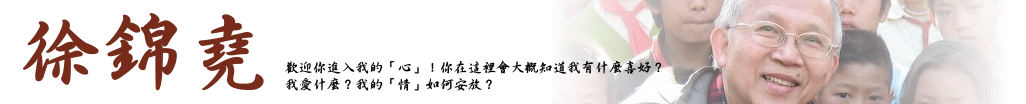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常5:我在這裡, 請派遣我 2025年02月09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經世的才華,若谷的虛心
讀經一:(依6:1-8):依撒意亞先知被召
讀經二:(格前15:1-11):要持守聽到的福音
福 音:(路5:1-11):耶穌召叫伯多祿和其他門徒
中國文化:高山仰止。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
西滿伯多祿看見這事,就俯伏在耶穌面前說:主啊,請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5:8)
主最後也顯現給好像是個流產兒的我。我實在是宗徒中最小的一個,不配稱為宗徒,因為我迫害過天主的教會。然而,由於天主的恩寵,我成了今日的我。(格前15:8-10)
伯多祿和保祿是教會中的兩位大宗徒,也是教會的兩大柱石,教會於每年六月廿九日,都為他們一起慶祝他們的瞻禮。但令我們十分驚訝的是,他們兩人在今天的讀經中,所表現的卻是十分的厚道、樸實、謙下和虛心。
伯多祿在看到耶穌所顯的捕魚奇蹟後,突然發覺耶穌在他的眼前無限地高大了起來,顯得十分莊嚴和神聖,自己卻相對地渺小不堪。他這種在神聖面前的自慚形穢意識,使他無論如何都感到不配與耶穌為伍。
保祿雖然已經完全皈依了,也承受了天主無數的恩典,為天主做了無量的工作和見證,他在格林多後書第十一章中,曾經細數他為主所受的各種勞苦。但他一生銘記著的,卻並非他的功勞,而是他的「不配」。
兩位大宗徒都有超越常人的經世才華,和驚人的毅力,他們甚至具有為義而殉道、為主而犧牲的大仁大勇,但他們所懷抱著的,卻是如深谷般的虛心。
這種虛心是什麼呢?為什麼往往越是偉大的人,卻越是虛懷若谷,而越是渺小的人,卻越是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目中無人呢?
我們在一些我們所敬佩的人面前,有時也會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甚至有一種不配做他們朋友的敬畏感。
當我第一次經過峭壁摩天的長江三峽時,第一次參觀巨大無比的廣西依嶺岩大溶洞時,第一次走近聲如雷鳴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時,第一次從故宮的太和門遙看金鑾殿在蔚藍的天空下,像一個巨人般仰臥在中國的大地上時……,我都有這種肅然起敬的感覺。
我驚訝上主的化工,我感念民族歷史的悠長,我緬懷著我們祖先曾經經歷過的奮鬥,所流過的血汗和淚水,和他們那些曾經擁有過的光輝歲月。
這也是孔子的門人弟子,在孔子面前所懷有的那種「高山仰止」的感覺,他們覺得孔子的學問、人品和胸襟,直如山高水畏,使他們起敬起畏。這也許亦是聖經上所說:「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開始」(德1:16)的那種敬畏之情。
在香港回歸後的首次法律年度開幕典禮中,其中的宗教儀式一環被取消了,也許是基於宗教平等的原則,不能單單採取基督宗教的儀式吧?但有部分的法官及法律界人士,卻自發要求舉行一台感恩祭,以表達他們的信念和心境。
這種心境就是:他們認為自己雖然有審斷是非曲直的職責,卻始終是以一個「人」的不足,去判決另一個同樣不足的人;他們要做的,幾乎就是神要做的工作。因此,這些法官和法律界人士,都深深的感到自己的不足和不配。所以他們都很願意藉著一個宗教儀式,謙虛地在上主面前祈求智慧、能力和大公無私的品格,以彌補他們先天的不足。
賈誼是漢朝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兼政論家,可惜懷才不遇,抑鬱以終。蘇東坡對這件事的感慨是:「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意思是,有些「聖賢」其實是有大才幹的,但他們終其一生,都不能實踐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這未必都是因為別人有問題,因為他們自己也許亦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而蘇東坡認為賈誼要負上的責任,就是他的不夠謙虛。蘇東坡對他的批評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度量小而又識見不足,顯然就是指的缺少虛懷若谷的胸襟。
聖經上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5:3)神貧最主要就是心靈的自空、倒空,對自己的一切自覺貧乏和不配,這樣才可讓上主去充滿。
伯多祿和保祿都是這樣的人,他們雖然有經世的才華,但卻有無比的虛心,那是一種自我懺悔、承認有限,同時亦完全相信、敬畏、依靠上主的無限虛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