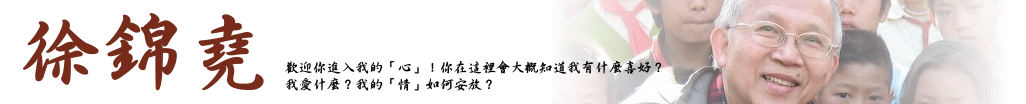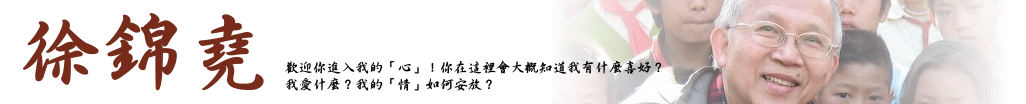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我懷著很沉重的心情寫這篇文章。起因是一位傳教士看完正委《籠中的鳥兒:中國宗教信仰實況資料》,感到「憤怒」,並問我有沒有看過這報告。我說看過了,不過當時沒有什麼感覺,因為我覺得正委從來就是這樣看中國的。但當我再讀這報告時,我卻有了這位傳教士的相同感受。
這報告並沒有說出中國宗教信仰的「實況」,「籠中的鳥兒」這個概念也是充滿偏見和貶義的,對中國不公平,也會被敵視中國的人利用去更敵視中國。
我相信讀過歷史或注意到政治現實的人,都會看得出,宗教從來就是在鳥籠中,分別只是大籠或小籠而已。任何政權都不會容許絕對的自由,而所謂的自由一定是以不威脅國家的穩定為界線。看看911和其後一連串變化的政治現實就可一目了然。
我不知道寫這實況報告的人有多認識中國?去過多少次中國大陸?在那裏生活過多久?有沒有深入的接觸過那裏的人?有沒有感受過中國的變化?
我自八一年已關心中國,八六年開始訪問,九四年經常去講學,九八年開始更是「每月」都往中國,一直到現在;至今已去了大城市小鄉村男女修院教區及大專院校等共五十多處。我不是單單去看看而已,而是講課、講避靜、辦活動,每個月都在十至十三天之間,每天講六至八小時。沒有人控制我要我講什麼、作什麼。我講的是教理、倫理、家庭宗教/民主教育、基基團、靈修、三願、梵二、聖經、中國文化。中國今天的確沒有很多的宗教自由,但如果說這是個「鳥籠」,這個籠也並不太小!
也許有人說我不過是被人利用,作為一個宗教自由的「花瓶」而已。但花瓶是只能用來裝飾的,讓你作花瓶的人決不會也讓你有任何作為。而我在大陸印刷和流傳的書,《正視人生的信仰》就有二十多萬冊,五本福傳小冊子更已達二百二十萬冊,連有「民主」兩個字的《家庭、民主、信仰》也已印了七萬冊!這一切對正委來說,似乎都不值一提。
鄭經翰在九七回歸前於有線電視的現場訪問中,曾問我有關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但他只要我回答一個是非題:「大陸還有主教坐牢嗎?」不理背景,不提歷史,不講因由,不談來龍去脈,更沒有前瞻。這絕對是一個充滿偏見和有了預設答案的訪問。我不知道正委的這個報告,會不會和鄭先生的這個訪問有點相似的地方?
* * * * * * * * * * 徐錦堯神父的忿怒使我驚訝
陳日君 徐錦堯神父說再讀了正委的「中國宗教信仰實況資料」感到憤怒,這使我很驚訝。其實,原文應是「中國宗教信仰自由實況資料彙編」,而徐神父在文中兩次把「自由」剔除。這是他的無意識的疏忽,抑或是他潛意識的逃避問題?
他憤怒的理由是這本書沒有說出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實況,但在這一百多頁的書中,他卻沒有指出究竟哪些資料不屬實。本人的言論在書中也占六頁之多,有不屬實的地方嗎?徐神父對我也憤怒嗎?
其實,徐神父自己也說「中國今天的確沒有很多的宗教自由」,又說「宗教從來就是在鳥籠中」,那麼為什麼抗議正委的書題呢?(至於說我們香港教會也已在鳥籠中,那倒要請教徐神父解釋一下了。我們還以為在香港宗教自由還未被侵犯哩!)
徐神父質疑,究竟書中發言的人對中國的認識有多少;我以為把書中多位發言人對中國宗教自由多年來的關注、研究和親身經歷加起來肯定不會少過徐神父(就算本人也曾七年功夫,每年在大陸七間修院服務足足六個月)。
關於徐神父的豐功偉業,我們當然心領。不過,我想請公教報編輯查一下徐神父已是第幾次告訴我們他做了這個又做了那個。我們並不集體失憶。
其實,分別不在於去過大陸多少次,而在於判斷和心態。如果徐神父以為中國政府已給教會足夠的自由,那麼他便是幫兇,也是鼓勵某些人推進一套落後的、極左的、害國害民的宗教政策;如果他以為他的所為所言能爭取他們改善政策,那麼事實證明他是天真!
徐神父批評鄭經翰問他「大陸還有主教坐牢嗎?」而「不理背景,不提歷史,不講因由,不談來龍去脈,沒有前瞻」。我倒要問問徐神父:難道「理了背景,提了歷史,講了因由,談了來龍去脈,有了前瞻」就可接受政府官員違反憲法而迫害那些只為了良心問題而不願屈服的主教、神父、教友嗎?徐神父當然也應該知道今天不單是地下教會,連多年忍勞忍冤和政府合作的地上主教和神父也因為爭取和教宗重建聯繫而受到極度的磨難。
講到這裏,我不想再多講了。希望徐神父快些醒回來,明白教區當局對他的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