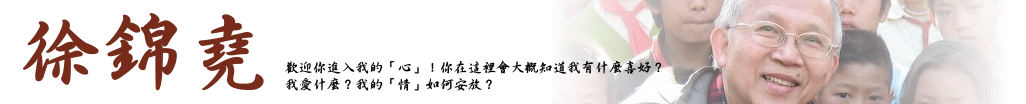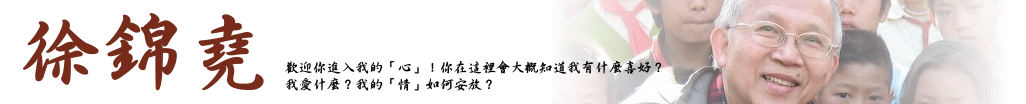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胡振中樞機與我 2011年02月07日
胡樞機是個很低調的人,但他的心靈生命很豐富、充實。
如果我用伯樂與千里馬、伯牙與鍾子期這兩個故事來形容我和樞機的關係,也許我在抬舉我自己。但我找不到更好的比喻,因為我們間的關係,事實確是這樣。他發掘了我,也是最明白我的宗教和政治理念的一位長者。
我是個鄉下人,本來有頗大的自卑感;我也不是教區神父中怎樣突出的人物。有一天,亞洲主教團在台灣開會,要求一位專家發言,樞機推薦了我。我不是什麼專家,但我努力準備論文,以免有負樞機的期望。這就是我十多年來穿梭台、港和大陸到處講學的開始。由於樞機的鼓勵,我慢慢變成了一匹跑得比我從前快了一點的馬。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港人大驚,移民者絡驛於途。在那個急劇轉變的時代,很多人要求樞機在許多事上發表聲明,但樞機沒有這樣作。我和一班有心人感到需要穩定人心,並能從世局變幻中,看到天主的保護。我們認為平信徒也可以按福音精神,表達對時局的關懷,選擇不同的回應方式。於是我們向教區要求成立「公教教研中心」,讓平信徒也可以在這方面作出貢獻,不必事事以教區最高領導人馬首是瞻。這種多元化的要求看似不可思議,所以教研的成立也久久未見實現;最後是胡樞機親自拍板才得成立。這是他的膽識、他的遠見。
令港人最分化的,莫過於政治,特別是對中國的態度。我個人比較親近中國,因為我熱愛中國文化,也接受中國的現狀。我認為這是我的「起步點」。我要建設中國而不是分析中國。我主張對香港有情、對中國有心,這使我和不少民主派朋友疏遠了。樞機有一次對我說:「你知道嗎?在香港有許多人喜歡你,也有許多人反對你。」我笑問:「哪邊的人多些?」他說:「也許是喜歡的人吧?」無論如何,他顯然就是這邊的人。
還有三件小事可以略窺樞機的內心狀態。其一是當我有一天偶然和他單獨在電梯時,他忽然舉起雙手對我說:「你放心去大陸做你要做的工作,我兩隻手支持你。」我當時很想哭,這樣的上司哪裡找?
另一次,我要作一件頗有爭議的事,去給他作報告,他贊成,但對我說:「徐神父,你今天是來通知我,不是要求我批准。」他信任屬下。
一九八九年他頒佈了《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當時牧函的起草者有我和另外三人。牧函頒佈後,許多人都認為那是我的東西,所以頗有微詞。他終於有一次在公開場合告訴我們,許多主教的牧函,甚至教宗的文告都是有人執筆的。但他加上一句:「只要我簽上了字,那就是我的牧函!」這是他與眾不同的胸襟。我會永遠懷念他。(2002年9月29日刊於明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