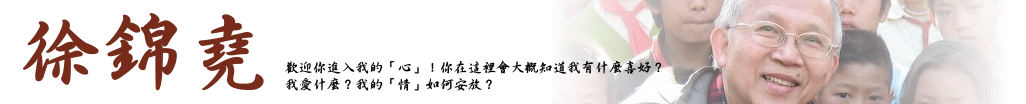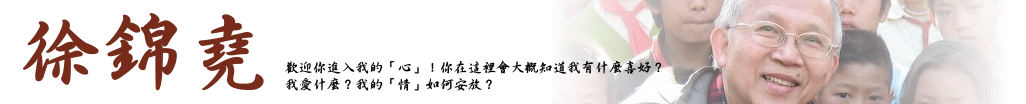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風雨晦明三十年 2011年02月07日
我今年五十八歲,做了神父三十年。如果你問我究竟活了多久?我可以毫不猶疑的告訴你:三十年,彈指而過;五十八載,談笑之間!
古人為父母祝壽,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的是父母福壽綿長,悲的是人壽終會有時而盡;今天的喜,必然也暗藏著明天的悲。保祿宗徒認定「世上沒有常存的城」(希13:14),臧克家譏笑那些騎在人民頭上想不朽的人是在妄想,因為「把名字刻在石頭上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這些都在告訴我們,人間的慶典,本來就是幫助我們淡化生死榮辱的默想機會;而人生一切「是非成敗轉頭空」,總有一天都會成為漁樵閒話,甚至化為灰飛煙滅、走磷飛螢。
我出生於貧窮的家庭,成長於微賤的環境。我能夠讀中學、進修院,自從家父于我九歲時去世後,我和母親、兩位妹妹等能夠平安渡日,過去幾年我還能僥倖略有所成,實在是全賴許多有心人士的扶翼與提攜,這一切我都會飲水思源、銘記於心。我至今堅持把「感恩」當作我整個生命的基調,而且不敢對生命有所挑剔或苛求,就是因為我相信「乞丐沒有選擇權」,而我原本就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乞丐。
我今天特意邀請了四位朋友證道,各人說出我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是希望我能為我的優點而感謝那位創造我的天主,為我的缺點而朝乾夕愓、戒慎恐懼。
今日(常年期第廿二主日)路加福音十四章教訓我們,當我們應邀赴婚宴時應謹慎選擇座位,不要只求上座、追名逐利,其中「滿招損、謙受益」的教訓,我們最易遺忘;對我這種稍有成就卻成就不高的所謂「半桶水」的人,「謙卑」更是一個我終生都要學習的課題。所以今日德訓篇也提醒我們:「你越偉大,就越當謙下;驕傲者的創傷,是無法醫治的。」
我幼承庭訓,先父教我以三字經、千字文等充滿中國文化色彩的訓蒙書籍,使我自幼便和中國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從此,我深深的愛上中國和中國的一切。我會為中國的優點和成就而自豪,會為她的一切缺點而難過憂傷。
有一次,我到了某一個修女院講大避靜,偶然拿起了九三年、九六年和九九年和她們一起合照的照片,竟然有一點「桃花依舊、人面全非」的心痛感覺。雖然那些脫離修道生活的人,畢竟只是少數,但那種因為她們的離去而讓我產生的傷痛之情,還是不能自已。其實這些修女與我非親非故,只不過是與我萍水相逢。我為她們悲,只因為她們是中國人,是中國教會的一部分。
亦因為我對中國和中國教會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情,所以我甘心為中國和中國教會奔波勞碌、付出一切。三十年來,我還沒有享受過教區給我們神父每五年三個月的大假,基本原因,是因為我很想為中國和中國教會爭分奪秒地多做一點事。我樂此不疲,真正原因也是因為我確實享受我在香港和在中國的工作,而且深感能在這個大時代中,特別在中國教會的重建過程中,能盡一分力,那確是一個機緣、一種福份。
我不敢爭千古,而只爭朝夕,並且要珍惜每分每秒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有一種時不我與的感覺。相信你們有些人已經知道,我的耳朵發炎已經三十多年,隨時會侵蝕我的大腦,讓我患上致命的腦膜炎。我每月回大陸,也隨時會遇上各種的意外。這種不安定的危機感,原來也是天主的祝福,使我好象伯多祿從安全的船上跳了下來,走在波濤洶湧的水面上,讓我可以隨時大喊:「主,救我吧!」
如果你問我在中國會以什麼原則辦事,我會在心中牢記「全面認識、深入分析、對症下藥、參與改變」這十六個大字,然後努力實踐的,卻是最後四個字:「參與改變」。我覺得馬克斯講的這句話很有道理:「哲學家們談論世界,但要點卻是如何去改造它。」
我很少以對抗的方式去辦事,對個人、團體、教會和國家都是如此。有一次我和一位民主派朋友開玩笑說:「我很相信你們都愛中國,也為中國好。但你們和中國對抗的結果,是中國政府不聽你們的,中國的百姓聽不到你們的。今天,至少中國的百姓還有機會聽到我說什麼;而我從來不必改變我的思想去遷就他們。」
我游走於兩岸三地之間,有時也到海外為華人教會做點事:我和基督教、佛教的關係都很好。這都是因為我相信立體的人生觀:即聖經啟示真理、有智慧的人(包括文化、自然科學、其他宗教)發現真理,我們則要經驗真理、活出真理。所以我相信一切的有心人都能殊途同歸,走向那唯一的真善美根源--天主那裏去。人類、甚至整個宇宙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我們需要的是互相欣賞、互相學習,並且快快樂樂的活在上主給我們創造的這個同一的小天地裏。
在過去這五十八年和這三十年中,我不敢說是歷盡滄桑,但亦絕不一帆風順。幸好仰賴天主的照顧,一切都已經化成了祝福。生命中的「風雨晦明」,不過都是身外事,心中如有「豔陽天」,那麼過去的一切一定都會全部變為甜蜜的回憶。就讓我以下列的小詩來作結:
主恩浩蕩三十年,始知人間別有天;
崎嶇世路猶平路,再共攜手三十年。(8/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