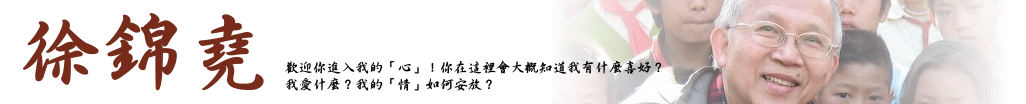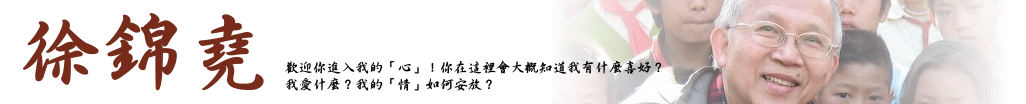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我為什麼愛教愛國? 2011年01月04日
我有一次在香港主持學生領袖訓練營時,曾邀請學生寫出自己的「墓誌銘」,以作為他們未來奮鬥的目標。為表示公平,我這個作導師的,最後也給學生們分享我的「墓誌銘」。
我當時的墓誌銘是這樣寫的:「這是一個愛教愛國的神父,他最大的遺憾是他的心載不下他的情──他對民族、教會和天主的大愛與深情。」
在香港,「愛國」曾經是一個貶義詞,因為有些人認為中國並不怎麼可愛。他們舉出了很多「中國不可愛」的理由,例如:中國並不現代化;儘管我們祖先有四大發明,但我們今日所享用的一切現代「文明」,幾乎全是舶來品;中國人髒、亂、吵;中國人喜歡「窩裡鬥」;中國人沒有禮貌、不尊重陌生人;儘管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和文明,但今天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與中國的傳統崇高文化並不相稱。許多人甚至認為,中國沒有人權、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是一個不堪居住的地方……。有理沒理的,講一大堆,結論是:不喜歡中國,不要做中國人。
也有些人認為不論是愛國也好,是民族感或民族主義也好,不過都只是一種狹隘的思想,是排他的、不能容物的,是世界許多地方動亂的根源。他們還振振有詞的指出:「你看,非洲某民族對某民族的種族大清洗,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等等,不都是民族主義惹的禍嗎?」他們更指出,愛國和民族感本來就與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氣魄不相稱,一個胸懷世界,放眼天下的世界一流大城市,為什麼要淪為中國的第二個上海或第二個廣州?
我的人生觀甚至宗教觀都和這些人不一樣。我這樣說,並不表示我的人生觀或宗教觀比他們強或比他們好。我有我的閱歷和思想,我有我的信念和修養。我不比他們好,也不比他們差;我就是我。
我愛教,也愛國;我愛天主,也愛世人;我不單胸懷天下,也扎根本地;我不單有世界的視野,也有民族的感情。這不單是我的人生觀,也是我的「信仰」,是我做人的最基本信念。這是我一生走路的「兩條腿」,沒有這兩條腿,我走不了這麼長的人生路。
在下面,我想介紹一下,我是怎麼樣發展我這「兩條腿」的,它們帶給了我多少面對生命的力量和歡樂。
我是一個鄉下人。先父徐麟祥從廣東省東莞縣移居香港,和家母陳肖珍結婚,於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的時候,在大嶼山島的大澳村生了我。先父在我九歲時去世,留下三十六歲的母親、七歲的妹妹笑芳、和未滿周歲的妹妹笑瓊。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四、五十年代的大澳,是一個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公路和任何現代設備的小鄉村。正因如此,那是一片十分乾淨的樂土,也塑造了我的「綠色」性格和我的環保思想。
大澳很窮,但我家更窮。我常向我的朋友戲言:香港最窮的島是大嶼山島,大嶼山島最窮的村是大澳村,大澳村最窮的一家就是我們徐家。
我後來能幹很多活、吃很多苦,多年來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五十四個地方,從東北的吉林到西南的雲南,從東邊的上海、寧波,到西邊的蘭州、銀川,什麼水土都能適應,什麼食物都能下咽,什麼床都能供我酣睡。這一切多少都與我窮苦的童年生活有關。英文有句諺語說:「乞丐沒有選擇權。」(Beggars have no choice)大概我也自視為乞丐吧?因為我確實曾經一無所有;「乞丐」又有什麼好挑剔的呢?孔子所說的「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大概也有這個意思。
我既是鄉下人,所以也自覺是大地的兒子,這就培養了我那強烈的鄉土情懷,也讓我有很強的超越大自然的直覺。所以當我讀梁漱溟先生的《鄉土中國》時,我很有共鳴。我對中國有很特殊的領會,在大陸看到那些名山大川時,也有很強烈的感受。這或許與我童年時與大自然的深入接觸有關。
在大澳,大部分的夏日黃昏,我都和其他孩子踏著田間的小徑、背著夕陽、聽著蛙聲、迎著拂面的和風,走向山腳的山坑去游泳。那時,基本上是天天天藍,點綴著潔白的浮雲,幻化出無盡的圖畫,也編織了我許多童年如詩的美夢。當時我的感覺不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而是「但得夕陽無限好,何必惆悵近黃昏」,因為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太陽是天天出來的,美麗的黃昏似乎也將永遠不斷的出現。
秋天的夜晚,更為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和一大群孩子玩「迷八仙」的遊戲,躺在大澳那著名的「鹽田」上,看到一輪皎潔的明月從東方冉冉昇起,我們就像躺在母親的懷抱中……。這經驗讓我有能力欣賞蘇東坡所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無盡藏也。」這是我對大自然由欣賞到驚訝、由讚嘆到崇敬的開始,也為我對「造物主」的信仰埋下了伏筆。更何況,我們全家都「拜神」,信奉很多中國人都相信的那種集儒、道、釋三家為一體的「傳統宗教」;我又是家中的唯一男孩,每天「上香」更是我的責任,所以神的觀念早就在我的心靈中暗暗地滋長起來了。
我沒有玩具。當時的孩子們都喜歡集體遊戲,不分階級、貧富和信仰,大家都像兄弟姊妹般一起盡情的玩。儘管我們的家是大澳中最窮的人家(我爸常生病,我媽是一個窮小販,我們全家就靠媽媽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肩挑著不同的小食去販賣,才能勉強維生的。)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和彼此的守望相助,卻使我深信,宗教人士所追求的「天國」真的可以蒞臨人間,理想的世界亦可以在地上出現。亦是這種環境培養了我對團體生活的重視和嚮往,並植下了我的教會感和民族感的種子。
我十三歲進了香港西貢的聖神小修院,因緣是因為我曾經遇上了幾位慈祥的神父和修士,因而對神職人員由衷的景仰。
我原本無力讀中學,全賴神父們給了我一個為貧困家庭孩子而捐出的獎學金,我才能繼續讀書。「神父」這個詞和它背後所代表的對人類的愛,就這樣深印在我的心中。所以,即使我今天做神父已經有三十年,我仍不忘常常鼓勵自己:要做神父,就要做一個有愛心的、樂於助人的好神父!
我的母親和所有親戚,包括最愛我的伯父和姑母,都反對我進入修道院。因為我讀小學時年年考第一,加上我是大澳唯一在「小學會考」中能考取到一個學位到香港市區去讀「初中一」的學生,那已相當於從前人們考到「秀才」或甚至「進士」了。所以母親和所有親友都把我看作是徐家的希望,甚至看成是「大澳之光」,入修院便等於使這些希望全部幻滅。何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對我這個「外教」的母親來說,讓獨生兒子作神父,使徐家的「香燈」從此無以為繼,確實太不可思議了!
修院並非人間天堂,長上、老師們也不見得時常講理;今日所追求的個人成長、良好的管理制度、尊重個人的情緒和私隱等等,當時並不流行,在修院生活中甚至完全欠奉。反而嚴謹、克己、服從、謙卑、守規……,你能想像得出的嚴格訓練,在我的小修院生涯中卻應有盡有。我今天較能嚴於律己、克苦耐勞,正是修院十三年嚴格訓練的結果。有人問我:「為什麼今天香港人承受逆境的能力是那麼的薄弱?」我想大概是與香港人過慣了幸福、順境的生活,缺少嚴格的訓練有關吧?
在十三年的大、小修院生活訓練中,我每星期辦一次告解(即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的具體實踐),每月見一次「神師」或導師去和他談我的靈性生活(即所謂的不斷「檢討」),十三年來從不間斷。我每天做公、私省察,也有一張自製的反省表格,提醒自己每天要做的功課、小克己、小小的愛德行動、特定的善工等等;連在寒、暑假回家渡假時,也忠實而用心地去完成這項任務。我是完全自由、自願、快樂地去做這一切的(有些同學則要經常勞動神師催促才去作這些事)。在這裡,我悟到道德的修養貴在自發、自由、自主、自願,凡事都要出自內心,由內至外、表裡一致,還要做得「自在」。一切的外在標準、外在壓力,都是很難使人真正成長的。難怪在我們十一位同屆進入小修院的同學中,只有我一人能升神父了!
我在進入小修院前,已唸完了五冊英語課本,但在進入修院時,還是要和其他同學由第一冊讀起。長上說這是遷就其他程度較低的同學,也是修練謙遜的方法。我對此毫無怨言,也不覺得自己的天才被埋沒。「滿招損、謙受益」這句名言,是我從具體的生活鍛鍊中悟出來的。對於我這種略有成就卻成就不高的所謂「半桶水」的人,「謙卑」是最難學到的一個課題,可幸我在修院時,已有了一點基礎。
我十分喜歡勞動,除每天勤於做例行的清潔工作外,每逢大節日修院大掃除時,更是幹勁沖天。因此,我對耶穌是「木匠」或「工人」的身份,感到十分親切。我更欣賞的,是天主教在靈修上的那句格言:「祈禱!勞動!」(Ora! et labora!)因為祈禱滋潤我們的心,勞動卻可使我們感到自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也許我當時已經知道「健康是革命的本錢」吧,所以我很喜歡體育運動,雖然身體因為先天不足、後天不良,而體型瘦弱,但在某次全修院的馬拉松賽跑中,居然榮獲第二名!
但因為我也喜歡音樂和彈風琴與鋼琴,自初中二起一直到升神父為止,已成為修院的琴師或指揮,所以每週總要利用幾次體育課的時間去練琴;有幾年還要教其他小師弟彈琴,所以常要犧牲體育。就在體育和音樂的雙重影響下,我似乎獲得了健康的成長機會。體育使我精神飽滿,音樂使我性情溫和,並培養了一種對生活品味的渴望和追求。
讀哲學時,曾經有一位教授因為一位同學上課時睡覺鬧出笑話而遷怒全班同學。他也責怪我,甚至說如果我不喜歡上他的課,我可以立刻離開修院。我沒有憤憤不平,也沒有受委屈的感覺。也許當時我已覺得人間本來就有許多不平事,多花點力氣在大不平事上是值得的,對小不平事,讓一步又何妨呢?
傳說中國某地有一條「仁義巷」,源於兩家在蓋房子時要爭地盤,其中一方求助於朝庭某位大官,大官卻給他們寫了這首詩:「千里捎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家人被這首詩所感化,因而讓出了三尺地,另一家亦受感動而讓出了三尺,於是便有了一條六尺寬的「仁義巷」了。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概也是指此吧?
在隨後的鐸職生活中,我受過更多委屈,但孔子的話常在我心中:「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上達,就是要達到人生更高的境界。我很相信,天主如果關了一扇門,就會為我開一個窗。痛苦,不過是化了妝的祝福。無論是多大的「絆腳石」,既然是石頭,不是也可以變為「踏腳石」嗎?做人如果能順天應人,做該做的事,人間的片時禍福,又算得上什麼?
我喜歡讀書,小時父親已把《三字經》、《千字文》、《幼學詩》等中國小孩的訓蒙書籍「紅皮書」要我背誦;進入修院又喜歡背誦聖經的重要章節。所以聖經和中國文化就在不知不覺中,在我的小小心靈內「交流」起來了。我今天幾乎是一讀聖經就想起中國文化,一讀中國文化就想起聖經。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是那麼的執著於「教會中國化、福音文化化」。
我在羅馬唸神學時,曾經利用三次的暑假,分別在英國的一所醫院、法國的一間中國餐館和德國的一間工廠中作過暑期工,所以我對工人的辛勞和苦況能夠較有體會。我是香港初期一個匱乏社會中的窮人;在歐洲,我看到甚麼叫「富裕社會中的窮人」。
我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晉升神父。之後我作過本堂神父,作過全港青年聯會的指導司鐸,作過小學和中學的校監和校牧,也教過中學生的倫理(德育)。我經歷過七零年代「認中關社」的熱潮,和青年人對權威的反叛。當時,如果你不跟青年人講理,不用他們聽得懂的、活生生的語言去接觸他們,你就會失去他們,他們會「用自己的腿」去告訴你:「我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道理』。」
經過九年的鐸職生涯後,我感覺到有使自己補充一下的需要,於是到英國的牛津大學兩年研究倫理教育或道德教育,隨後即寫成了六本一套的倫理書,並在這基礎上,我主編了《香港情、中國心》的三十三個單元課程。教研中心於八六年成立後,更開始了我不斷往台灣、中國大陸的工作,有時也要到星加坡、馬來西亞或全球其他華人地區去為當地的華人傳福音、講做人的道理。
我現在所深信和要傳佈的,是一種我十分相信的信仰:「正視人生」的信仰。我認為信仰要和生活結合,聖經和文化、宗教和社會也要相結合和相適應。教會除宣講天國外,更要聯合世上所有懷善意的人們(不分宗教和種族),去重整世界的秩序,為一個更快樂、更人道的社會而奮鬥。我現在致力推動的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公民教育等等,便是要為未來的新社會鋪路。
我是香港人,但我堅信我們有三重身分:香港人、中國人、基督徒。我們要扎根信仰、投身社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注目永恆。
我也相信所謂的「立體人生觀」,一切真善美的思想和行為,都可助人走向至善,或者是說到達神的懷抱中。有一次,當我在遼寧省的撫順市參觀完雷博物館後,我在他們的嘉賓名冊上寫了這幾行字:「我喜歡立體的人生觀,所以無論是基督的博愛、佛佗的慈悲、孔子的仁愛,或雷的犧牲,都值得長照宇宙,永留人間。」這就是立體的人生!
做神父除了要回應天主外,也要回應世間的真正而永久的需要。聖召完成的時候,就是我回歸父家的時候。這種聖召是快樂的,我慶幸能走上這條聖召之路,並且已經做了整整三十年快樂的神父--愛國愛教的神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