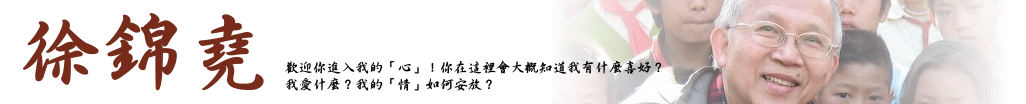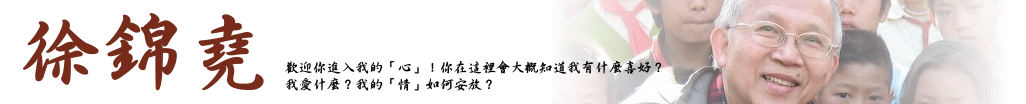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寄情於天地、盡性於人間 -- 算一個晉鐸廿五年的賬-- 2010年12月28日
在永恆的歲月中,廿五年還不到一瞬之間,但對我來說,這是帶來永恆的一瞬。如果我未曾完全善用這過去的廿五年,我願盡力去善用我未來餘下的時間。
我的過去,可用性、情兩個字來代表。我重視性,也重視情。
性是本性、人性、物性、天性的性,是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的性。情是友情、愛情、親情、感情的情,是歐陽修所說「人間自是有情癡」,或李賀所說「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情。今日福音中的客納罕婦人這樣深愛女兒,為了要求耶穌治好女兒,甚至被貶為「小狗」也不以為忤,也可說是情癡的一種。
我一向相信人生觀該是「立體」的,它有三面:第一是天主啟示的真理,第二是我們的祖先、聖賢、科學家所發現的真理,第三是我們今日在具體的生活中所經驗的真理。啟示的真理、發現的真理、經驗的真理,都是由上主而來的真理,是天主在造物時,放在一切受造物中的「性」。
要做一個完人,或甚至要做人,就是要按照天主所造的本性,即按天主原定的計劃去生活,使萬物能各展其性,使人人能各盡其性。這很相似中國人所說的「五倫」。
廿五年來,或者更準確一點來說,自從我懂事以來,我一直喜歡去思考,去探索;思考生命、宗教、國家、世界的問題,探索生存、活著、信仰的意義。
先父在我三、四歲時已教我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幼學詩,我在中學時也曾嘗試背誦聖經。因此我愛聖經,也愛中國文化,所以我十分重視中西文化的結合和互補,更肯定中國文化在信仰中的重要地位。
我來自一個外教家庭,我的母親和兩位妹妹都是在我入修院後才領洗的;而先父卻在還未接觸到天主教前就離開了我們。這使我很認真的去思考領洗和救恩的關係,特別因為這牽涉到我的父親和我大部分親人的得救。
在我十三年的修道生活和後來的兩年進修生活中,我經歷過六個修院、九個院長,有超過四十多個國家的同學。我的信仰成長在梵二的前後,經歷過最保守和最前進、甚至最激進的陶成方法。我在歐洲、美洲、非洲、東南亞、台灣、中國大陸,都有過或長或短的生活體驗。在修生的年代,我做過醫院、酒樓、工廠的工作。升神父後,我做過副本堂、本堂、校監、學校神師、倫理科教師、教友總會、青年聯會、教研中心各種工作。我曾在七十年代和青年人攜手經過那轟轟烈烈的「認中關社」階段,也曾在寧靜的長洲向印度的Fr. De Melo 及日本的Fr. Oscida 兩位天主教禪學大師學習靜坐祈禱。我喜歡傳統的神學,也喜歡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邏輯學、政治學等人文科學。我願為教會而奉獻一生,我也有強烈的愛國情懷……。
我的經驗是多樣化的,所以也必然是駁雜、不純的。但我會在這些經驗中不斷的反省、回顧、思考。我常問:天主,你要「我」作什麼?你要「我們」作什麼?你的聖意在那裡?你對我們本來有的是什麼計劃?這是我對生命「本性」的追求。
由於我的思考習慣,許多人誤以為我是個很理性的人。所以在一次教研中心的長期課程後,有一位畢業學員來對我說:「神父,我很慶幸能修畢這個課程。因為我們本堂神父原本曾勸諭我不要來參加這個課程,因為他說徐神父太理性,不適合普通教友。」
其實,我從來不是個太理性的人,有時我甚至認為自己不夠理性。我的思維有點膚淺,對事情了解不夠深入,學問也遠遠未夠成為一家之言。因為我同時也是個感性、重情的人。
我曾經為花木而癡、為星月而迷。我喜歡在海邊、在山上、在溪旁,聽澎湃的海濤、淙淙的流水,欣賞鳥兒蜿囀的啼聲、看白雲翩翩的飛舞。我曾經獨自在天台上,長久地凝神看著夜空中閃爍的星星,在長江三峽的遊輪上,擁著午夜的巫峽和那灑在江上的月亮銀輝而整夜無眠。我很嚮往「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境界,憧憬著「天人合一」的來臨。
在最近我為天主教學校編寫的公民教育課程中,我對「香港情、中國心」這兩個情字和心字,有很特別的感受和喜愛。中國公民不單要認識中國的河山,也要對這個河山有情;不單要認識中國歷史,也要以大願的心,去肩擔著歷史的重擔;不單要認識中國的人民,也要以大慈悲的心,去和中國的人民同甘共苦。這就是情,是對國家、民族的情。這個情會帶導我們去「足踏塵世路,肩擔古今愁」。
我喜歡工作,我也確實享受我的工作。我不需要太多休息,因為我在作不同的工作時,也能休息。我曾經為工作而廢寢忘餐,為完成一件工作而大喜若狂。我可以很專注地工作,投入每一個工作,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在工作時,我的心常像有一把火在;在寫作時,我很多時都會情不自禁。
有人說我愛哭,但我多數只為三、四樣事而哭:為耶穌、為我去世的父親、為國家民族。兩年前當我寫「六四祭先烈」的禱文時,我曾經在房間裡邊寫邊哭、大聲地哭。當我在一九七四年第一次踏足中國大陸時,那時中國還未開放,我在一間酒店的房間中秘密地作彌撒,這是我在夢寐以求的中國大地上所作的第一台彌撒,這台彌撒我作了足足兩個多小時,因為有一個多小時是在眼淚中渡過的。
歐陽修說「人生自是有情癡,此事不關風與月」。太上可以忘情,無靈之物可以無情,而為情所累或為情所滋潤的,正是我們這些靈明的人類、有情之輩。風和月本來沒有什麼,但對某些面對風月的人來說,風月之外卻是別有令人動情的因素。
我小時候住在大澳,家境十分窮困,爸爸一直生病,母親做小販維生。家裡養了一隻狗,牠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一天,那隻狗死了,我哭得很傷心,爸爸就把牠葬在屋後的荒地上,還插上兩支蠟燭,就好像是死了一個人一個我的親人一樣。我現在知道大澳並沒有給狗「送葬」的習俗,我不知道爸爸這樣作是不是在「葬狗示兒」。他已在我九歲時去世,我亦再沒有機會去向他問個明白了。
廿五年的鐸職生涯,要感謝的人很多。最老套但最真實的,當然是要感謝我的父母。數年前,有一次母親來找我吃午飯,她忘了下車。後來她對我說,可能是去世的父親牽著她、阻著她,不讓她下車。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我可以每個星期請她吃飯,卻從來沒有請過爸爸吃什麼。但我知道爸爸不會這樣小氣,因為天主會因為我而報答爸爸,也會因為爸爸而祝福我。今天我也要特別多謝媽媽來和我一起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她今年已經八十歲,我也想請大家和我一起感謝她。
作為一位神父,我也想特別多謝一些使我成為今日的我的教友。他們中的一位和我一起成立了教研中心,一位促成我在台灣的工作,另一位使我能作大陸教會的使徒和僕役,一直到今天。教研中心今天能有少許成就,更是許多許多教友義工們辛勤努力的成果。
當然,在一切之上,我不能不多謝天主。在《聊齋》中,田七郎的母親對田七郎說:「你知道嗎?人家待你好,你就得幫人家分憂;人家給了你好處,你就得幫人家解決困難。有錢人可以拿錢報答人家,我們窮人報答人家什麼?莫非拿你這條命去還禮嗎?」在天主前,我們都是一無所有的貧窮人,天主對我們好,我們除了拿出我們的生命以外,還有什麼?
所以我今天要在上主和大家面前作一個許諾:為過去所有日子感謝,為未來所有日子祈福;願全意全情為教為國,願盡心盡性愛主愛人。
藉著你們的祈禱和支持,我相信我可以一生實踐這個許諾。
(徐錦堯神父晉鐸銀慶感恩祭講道詞 8-199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