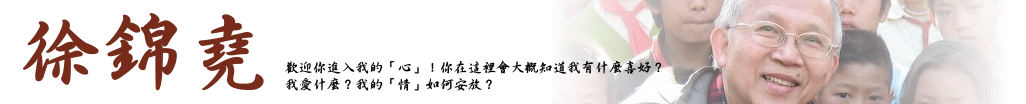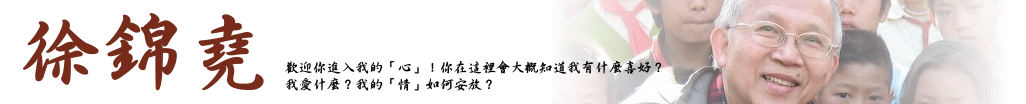| 我喜歡美國,但也許不能再去美國了。
事緣零三年二月,洛杉機華人團體邀請我為他們作培訓課程,北美洲其他華人團體知道了,都希望我順道往訪。最後的決定是三天在溫哥華,一天在西雅圖,八天在洛杉機。
我在溫哥華為華人作了三天演講後,於二月十二日由友人開車送我經Lynden關往西雅圖。這日剛好是武檢小組向聯合國提交報告的前兩天,這時美國的反恐警戒是橙色(很高!)
當關員知道我是應邀往西雅圖為當地華人天主教團體作培訓時,要求我出示邀請信。我的一切邀請信都是中文的,但有一個行程表是英文,裡面寫的是彌撒、觀光、靈修講話、Workshop等。一聽到Workshop,關員立刻問我How much do you get paid? Who pays for it?我說我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整個課程都是免費的。我還說香港教會對workshop 這個字的解釋不過是等同於seminar,與work無關。但每當我要作任何解釋時,那個關員總是很凶、很粗暴而大聲的說:You listen to me!!! 任何解釋他都不聽。
這時是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左右,西雅圖的朋友希望我們中午到?。我們選擇在這兒過關,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偏遠的關口,過關車龍會短一些。
在無法說服關員的情況下,我們只有致電西雅圖的朋友,請他們立刻給我傳真一封邀請信,說明這是一個「無酬金的」邀請。我們原希望這信能直接傳真到海關,但他們不允許。我們只好問可否傳到Richmond朋友處,我們往那裡取信,再從那裡附近的Peace Arch過關。關員答應了。於是我們到Richmond取得傳真後,再往Peace Arch。這時已經是中午十二時左右。
我們一到Peace Arch,關員從頭問我過關的一般問題。最要命的一句是問我「曾否被拒絕進入美國」。我回想廿多年來走遍天下,從未被拒絕過,以前兩次來美國,也順利過關,所以「條件反射地」答以「沒有」。他立刻說我「說謊」,因為我剛好就在兩個小時前被拒入美國!
我立刻道歉並強調這純粹是一個「語言上」的誤會。因為我正在為解決過關的事而奔走,海關並未斷然拒絕我過關,只是要求我先拿到一封英文邀請信而已。整個上午其實是「同一的一次」過關,仍然是一個「進行式」,而不是一個完成式,並立刻把手上的傳真信給他看以資證明。
那關員忽然問我在什麼地方唸書。我答以在羅馬。他立刻說我的英語沒有問題(大概他不知道羅馬是說意大利語而非英語),應對「曾否被拒絕進入美國」這問題不會產生誤會。我說假如我要欺騙,何必去拿邀請信呢?整個處境都顯示出,我完全沒有欺騙的動機和必要。
那關員不接受我的解釋,反說我分別由兩個關口過關正是存心欺騙的證據。我再一次解釋經兩個關口的理由,而且那也是Lynden關員所允許的。他再一次表明不接受這解釋,還說要取消我原有的美國簽證。
最後的結果是,他果真把我的美國簽證拿去注銷了,並說我可以去溫哥華美國領事館向有關人士解釋,重新申請美國簽證。然後他要我簽署一份文件,內有兩個選擇:一是取消這次行程,並接受美國簽證被注銷的事實,裡面寫的裡由是:It seems that he is deliberately cheating。他用的是It seems,並未完全肯定。
另一選擇是向美國法院上訴,但大約要排期一個半月(四十五天)。對我這個只在美國停留八天的人來說,兩個選擇其實只剩下一個,就是認罪、取消行程、喪失美國入境簽證。
十分奇怪的是,當他把注銷了的簽證還給我的時候,他忽然加了一個按語,他說我所犯的是一個Honest mistake。待他離去後,旁邊的另一關員也說:「我們不能不從嚴,因為太多人想欺騙美國!」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在It seems(未定案)和 honest mistake(誠實)這兩大因素下,我仍然會因為「不誠實」的罪名而被判罪?他們又為什麼要把我這個絕對無心欺騙的人和其他的欺騙者放在一起處理?
* * * *
我第二天一早就去美國領事館準備申訴。令我更驚訝的是,我在領事館中竟然不獲任何官員接見,只有一位「詢問處」的人來問我幾條極簡單的問題,然後叫我回去再預約來領事館面談的時間!
這位「看門人」簡單的告訴我,預約要三、四天,給簽證的時間至少要一周以上。我立刻告以沒有這個時間,因為我必須在次日往洛杉機,並呈示我的機票,希望能得到領事館的幫助。他表示我除了回去等候以外,沒有辦法。我問他可否給我「三分鐘」的時間向他的上司陳情。他一口拒絕了,並認為他已經替我傳?了我要講的全部。我告訴那職員,我是受到不公平對待,難道就沒有任何補救的辦法嗎?他再不看我一眼,就走了。
就這樣,我莫明其妙地被取消了美國的入境簽證,讓西雅圖和洛杉機的朋友們白白地等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理由竟然是在Honest mistake下的一個未經證實的「欺騙」之罪!
在這事上,我經常講的道理又一次受到考驗:我真的相信不幸可以變為祝福嗎?我真的以為一切絆腳石都可以變為踏腳石,而天主能從壞事中產生好事嗎?
這次在美加的日子,正是我六十大壽的日子。這個意外連同三個月前腦袋生的那個「瘤」當然也是天主送給我的壽禮!它讓我再一次在政治和信仰上作了很深的反省。
在政治和國際事務上,我反省到:
一、從關員和使館人員身上,我看到很多人際關係的「反面教材」,足夠我作多年的講道。我不主張在公事上講人情,但公事不可以有「人情味」嗎?我認為辦事要公正,但也要容許解釋和讓錯誤得到糾正。連在公事公辦的時候也是有很多弱小者要照顧的。
二、海關是一國之大門,款待各方來客,關員本應理性而熱情、有禮而樂助。是什麼讓我們的世界變得互相提防、互不信任呢?聖經的待客之道(hospitality)為什麼會變得那麼難?
三、我更明白馬克斯所說的「人性的疏離」或「非人化」是什麼一回事。官僚主義、以官老爺君臨天下的姿態按章辦事等,正是這些「非人化」的罪魁禍首。
四、我喜歡美國人講的「美國精神」,那是自由、民主、人權、理性、人道的綜合體。但當我在一天內經驗到兩個海關的關員和美國領事館人員辦事方式的荒謬性的時候,我知道所謂的「美國精神」不過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它很容易被不肖的辦事人員所破壞。
五、今日世界看到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即不理世界的公論,只知獨斷獨行,很可能也是潛藏著的「另一美國精神」。所以我們不可能期望坐在華爾街掌握著世界經濟命脈的大員們會關心亞洲的金融風暴;而坐在五角大?、握著弱國生死的軍閥們又怎會同情巴肋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命運呢?
六、所以我從此會更多宣講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理想。柏拉圖所說「人是自私的、集體的人則集體自私」果然是千古名言。中國將來強大了,也是多半會欺負弱小國家的。所以基督徒必須活出一種「扎根信仰、放眼世界」的信仰,以促進世界大同,打破人間隔閡。我知道在美國中就有很多有良知的美國公民,他們也願意為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平等而奮鬥,我所認識的美國朋友中,就有很多這類人。美國是很難被世界改變的,只有靠美國人從內部去自我改變了。我希望有一天,美國也能「表裡一致」地,活出他們所宣?的「美國精神」,這正是美國能從基督處獲得的「救恩」。
七、美國的軍力,已經是排在她後面的九個強國軍力的總和,但我看美國的當權者還是有很大的集體恐懼感,這才導致了關員們的非理性舉動。美國追求的是絕對的安全。但她忘記了聖經說的「世上沒有常存的城」,而且也只有仁者才可以無敵於天下。
* * * * * *
在個人和信仰層面上,我也反省到:
一、我再一次明白什麼叫在個人能力範圍外的「邊際境遇」,那是我經驗天主照顧、依靠天主、學習服從、學習交託的最佳時刻。想不到這幾天我的祈禱竟然分外熱切!我也再一次明白什麼叫「人總有不可為、不能為,或為而無所成的時候。」對我這個到處受歡迎的人來說,這也是我真正學到謙卑的機會,並領悟什麼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二、在困境中,我全身的思考力、應變力等都好像大量地湧流出來,整個生命都像是處在最高戒備狀態中。那是一種難得的感覺,儼然是生命力的一個大檢閱。
三、工作本是為了提昇人性,不是為了泯滅人性。幫助有需要的人始終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本分,所以在我們的任何工作中,愛與同情、關懷和幫助一定要佔最主導的位置。
四、另一方面,溫哥華很多朋友卻在這意外中為我盡力奔走,真是「人間有情」!他們和海關老爺們高傲而冷酷的嘴臉形成了極強烈的對照。
五、更妙的是,因為我不能去洛杉機,所以大家都為我想辦法如何補救。最後我們採用了網上聚會(Net-meeting) 的方法,讓我安坐在溫哥華朋友家的一部電腦前,卻能和洛杉機的朋友們見面。我能見到他們,他們也能見到我;我可以向他們講,他們也可以向我問!
六、為了這個網上聚會,美加兩邊的朋友們日以繼夜的工作,終於以最原始的方法去完成了最不可思議的任務,而且效果超出理想:我講的開心,洛城的人也聽得滿意。足見有志者,事竟成。
七、我已去了大陸五十多個地方,要再輪一次也是不易。如果有一天我能安坐在香港,然後啟動大陸教會多個地方的電腦,同時為他們上課;那麼這項新工作應該就是因這次意外而誕生的了!這不是天主從壞事中產生出好事來嗎?
八、去不成美國,得益最大的當然就是溫哥華的教友了。這正是「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有何憾呢?何況,美國的朋友也不是沒有聽講的機會呢!
九、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誰知道如果我去了美國,反會遇上另外的其他災難?在美伊危機中,去不成美國,也未始不是好事。
十、最後也是最弔詭的一點,就是在政治「最民主」、宗教「最自由」的美國,竟然就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現在為止唯一的一次不能去「傳道」的地方。而在某些人眼中認為沒有宗教自由的中國,我卻竟然可以為基督的福音而連續鞠躬盡瘁了十多年!
十一、美國仍然是我愛的一個地方,我更愛的是美國的華僑朋友。我在這事件中曾答應過會給他們「賠償損失」。待我回香港後,我會再申請美國簽證,如果再失敗的話,那我只好說:「再見了,美國!」 |